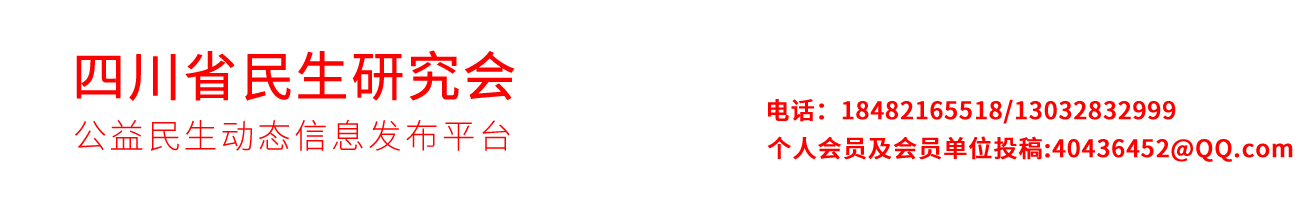文/陈仕猛
李时珍是否任过太医院院判?他什么时候进入太医院,又是何时离开太医院?由于什么原因离开太医院?对这些问题,医史学界、地方文史界一直争议很大。笔者试在前人论述基础上,再作一番探索和考辨。
一、李时珍是否任过太医院判?
太医院是大明帝国最高等级医疗机构,行政长官为院使,正五品,副长官为院判,职数两人,正六品。[1]院判是仅次于院使的高级医官。最早记述李时珍曾任太医院判的,大致是蕲春先贤、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、学者顾景星(1621—1687)。他写了一篇《李时珍传》,该《传》有两个版本,一是他早期撰写的,被康熙三年(1664)本《蕲州志》卷十《艺文志》收录(下称“《李时珍传》初稿”);一是他后来修改过的,在他去世之后、其子顾昌等人搜集整理,收入康熙四十三年(1704)刊刻的《白茅堂集》卷三八(下称《白茅堂集·李时珍传》或“《李时珍传》定稿”)。两个版本字句有点差异,如,前者说“楚王……荐于朝,授太医院院判,数岁告归”,后者说“楚王……荐于朝,授太医院判,一岁告归”。康熙《蕲州志》卷八《人物志·学行》也有“李时珍传”,成稿时间大约迟于顾景星所撰《李时珍传》初稿,也说“升太医院判”。此后三部《蕲州志》都沿袭这一说法。
但是,李时珍本人在《本草纲目》卷首“辑书姓氏”中,自称官职为“敕封文林郎、四川蓬溪县知县”,在卷一《序例上》“历代诸家本草”中,称官职为“楚府奉祠、敕封文林郎、蓬溪知县”;李时珍次子李建元在《进本草纲目疏》中,说父亲“原任楚府奉祠,奉敕进封文林郎、四川蓬溪知县”;《明史》卷二九九《方伎列传》中“李时珍传”,说“时珍官楚王府奉祠正”。这些文献资料,都没有提到李时珍任过太医院判。李时珍墓碑具有“盖棺定论”的意义,碑上也只刻有“明敕封文林郎”字样。文林郎,是明代正七品文官的散阶(荣誉性官衔)之一。知县为正七品,初授承事郎;任满三年考核称职的,升授文林郎。父、祖可因子、孙显贵,封赠如同子、孙一样的官职或官衔,“生曰封,死曰赠”(活着的称“封”,死去的称“赠”)。李时珍长子李建中于万历三年(1575)任四川蓬溪县知县,万历六年(1578)左右,因考核称职,升授文林郎。可见,李时珍所任实职,是楚王府奉祠正(正八品),因长子李建中显贵,才奉敕进封文林郎、四川蓬溪知县这一虚衔。
新中国成立后,李时珍曾任太医院判的说法受到质疑。如,著名记者、作家张慧剑在传记文学作品《李时珍》一书中,说李时珍在太医院“所任的官职很低”。[2]上海中医学院(上海中医药大学的前身)中医学史专家吴佐忻所编《李时珍生平年表》,认为李时珍在太医院“最高职务不会超过御医”(御医为正八品医官),而不是顾景星所说的太医院判。[3]著名哲学家唐明邦所著《李时珍评传》,认为“史称曾任太医院院判……不确”。[4]曾任湖北中医学院(湖北中医药大学的前身)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李裕,长春中医学院教授郎需才,蕲春县博物馆馆长王宏彬等人,都撰文论述李时珍没有任过太医院判。[5]
也有坚持“李时珍曾任太医院判”说的,如,著名医史学家、中华医史学会首任会长王吉民所编《李时珍先生年谱》,以顾景星《白茅堂集·李时珍传》为依据,说李时珍任过太医院判。[6]曾任湖北省中医药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室主任钱远铭主编的《李时珍史实考》,力主“李时珍曾任太医院判”说,认为顾李两家世代相交,顾景星受李时珍后代之托,对李时珍生平比较了解;清康熙《蕲州志》和后来几部《蕲州志》以及《黄州府志》《湖广通志》,都记载了李时珍任太医院判,这些地方志都是地方政府所修,更为可信;李时珍医院医史文献馆所藏四贤坊表碑上,明确刻写了“太医院判李时珍”,“尤为确证”。[7]
我们先审视一下顾景星所撰《李时珍传》,看它是否为信史。李裕、王宏彬曾对此作过探讨,认为顾氏所记并不绝对可靠,准确性、真实性应当存疑。下面再加深入考述。
顾景星(1621—1687)是在李时珍去世三十年左右才出生的。明末战乱,特别是张献忠屠蕲时,李时珍孙辈中最有名望的人物李树初誓死抵抗,他本人和多个子孙惨遭杀戮,李氏家史资料失传,最典型的例子是,李家后人居然对李时珍祖父的名字和基本情况一无所知。《白茅堂集·李时珍传》记述李时珍的祖父,仅有“祖某”二字,这两个字可有可无,没有任何实际意义,反而恰恰表明李氏后人和顾景星对李时珍祖父情况茫然无知。顾景星所撰《李时珍传》初稿,不提李时珍祖父,连“祖某”二字都没有。
顾景星在《传》中说,李时珍开过一个“附子和气汤”的方子,打消了富顺王因“嬖庶孽”(偏爱小老婆生的孩子)而打算废立王储的念头。殊不知,废立王储,自有朝廷制度规定,不是哪个想废就废、想立就立的;而且,第一代富顺王朱厚焜(1498—1576)素有“贤王”之美誉,说他“嬖庶孽”,似乎是给他泼脏水。事实上,他的元妃没有亲生儿子,即根本没有嫡子,受封富顺王长子的,为庶一子朱载垬,万历四年(1576)六月朱厚焜去世后,载垬于万历十年(1582)四月袭封富顺王。[8]可以说,顾景星所写李时珍与富顺王府这个故事,一点也不可靠。李时珍给富顺王府成员治病的事儿倒是有,《本草纲目》卷六《火部·火之一》“灯花”条,就记载了他将杀虫治癖的药做成丸子,治好了富顺王一个孙子嗜吃灯花的怪病。
在《李时珍传》初稿中,顾景星自己都承认,他所记“(李时珍)先生轶事”,是“儿时于里中闻知”的,即小时候在街头巷尾听说的。《李时珍传》定稿与初稿大同小异,尽管删去了“于里中”三字,但改变不了《李时珍传》取材于民间故事的性质。顾景星在为李树初撰写的《墓志铭》中,说到撰写李氏四贤传(包括《李时珍传》《李建中传》《李建木传》等),依据的是李树初之子提供的资料,有可能是明知“授太医院判”之类情况不实,但碍于两家交情,不好不写。[9]还有,顾景星是采用文学笔法撰写人物传记的,如,他说李时珍诞生时,“白鹿入室,紫芝产庭”,使用的是古代中国典型的拔高和神化伟人、名人的手法。
总之,顾景星的《李时珍传》,所记李时珍事迹,并不那么可靠,只宜作个参考。决不能用《传》中所记“授太医院判”,作为李时珍曾任太医院判的证据。
至于清代后来三部《蕲州志》以及《黄州府志》《湖广通志》,所记李时珍任太医院判,都是沿袭顾景星《李时珍传》和康熙《蕲州志》的说法,同样不足取信。《明史》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等国家级官修著作,成书于《白茅堂集》之后,均未采信顾氏之说,记述李时珍官职时,只说“官楚王府奉祠正”,而不说“官太医院判”。
我们再来审视一下四贤坊表碑所刻“太医院判李时珍”,看它是否可以作为铁证。王宏彬曾作过考述,这里仍有必要再加探究。
这块碑,上有“六朝文献,两镇干城”字样,中有“授太医院判李时珍、山西副使李树初”“赠中宪大夫李建中、李建木”字样,右侧称初立于“天启甲子”,左侧说重立于“光绪乙巳年”。天启甲子,即天启四年(1624),彼时,碑上提到的四人中,李时珍已去世三十余年,李建中、李建木也已去世,唯独李树初健在,而且尚在官场。李树初官至山西按察副使,明末死于张献忠屠蕲,到清初,顾景星应李树初次子李具庆之请,撰写了《明中顺大夫山西按察司副使李公墓志铭》[10]。《墓志铭》说,在烈皇帝(即崇祯皇帝朱由检)诛杀阉党首领魏忠贤之后,李树初升任山西按察副使,因协调外邦、安定边境有功,“覃恩授中宪大夫,请移封本生父,而自以中顺大夫落职”。《明史》卷二三《庄烈帝本纪一》记载,天启七年(1627)八月,明熹宗朱由校薨逝,皇五弟信王朱由检继位,十一月,魏忠贤被缢死。如果按《李树初墓志铭》所说,那李树初任山西按察副使、朝廷追赠李建中(李时珍的长子,李树初的生父)、李建木(李时珍最小的儿子,李树初的嗣父)两人中宪大夫衔,当在天启七年(1627)十一月之后。但是,《明熹宗实录》卷八三,天启七年四月壬戌条记载:“升大同府知府李树初为山西按察司副使、雁平道。”又据《万历四十七年己未科进士履历便览》[11],李树初于天启甲子升郎中(正五品),丙寅(天启六年,1626)升大同知府(正四品),丁卯(天启七年,1627)升山西副使(正四品)。可见事实是,李树初在崇祯皇帝尚未继位、魏忠贤尚未伏诛之前,即已升任山西按察副使。显然,顾氏所撰的《李树初墓志铭》,与他所撰的《李时珍传》一样,可信度不高。[12]
明代正四品文官,初授中顺大夫,升授中宪大夫。按照制度,天启六年,李树初由户部郎中升任大同知府,可以授中顺大夫衔;天启七年四月,李树初又升任山西按察副使,在此之后,他才可能将正四品文官升授的中宪大夫衔,移赠给生父李建中和嗣父李建木。因此,光绪乙巳年(即光绪三十一年,1905)所立的四贤坊表碑,说“天启甲子”原碑上就刻了“授山西副使李树初”“赠中宪大夫李建中、李建木”,显然与史实不符。如果说天启甲子就立有这个碑,那就成了提前几年预知李树初已晋升山西副使,预知李树初已为其生父、嗣父请赠中宪大夫了。说“天启甲子”初立,可能是当时人们记忆失误。
“六朝文献,两镇干城”坊,是一座与四贤坊表碑密切相关的牌坊。康熙三年(1664)本《蕲州志》卷四《建置志》说:“六朝文献两镇干城,在宾阳门外,玄妙观前,为同知李建中、副使李树初立。”乾隆二十年(1755)本《蕲州志》卷三《建置志》、咸丰二年(1852)本《蕲州志》卷四《建置志》、光绪八年(1882)本《蕲州志》卷四《建置志》,都说:“六朝文献两镇干城,在东门外,为知县李时珍、同知李建中、副使李建木、兵备李树初建。”四部《蕲州志》的《建置志》,所记“六朝文献,两镇干城”坊,只提李时珍受敕所封的“知县”,不说“授太医院判”。可见,四贤坊表碑所刻“太医院判李时珍”,其实是源于顾景星所撰的《李时珍传》和《蕲州志》的《人物志·李时珍传》。而顾氏《李时珍传》本来就不可靠,那据此所刻的四贤坊表碑,岂能作为“李时珍曾任太医院判”的铁证!
如果李时珍确实任过太医院判,那在《本草纲目》这部凝聚了他毕生心血的医药学巨著中,只写正八品实职“楚府奉祠”、正七品虚衔“文林郎、四川蓬溪知县”,而不写正六品实职、高级医官职务“太医院判”,这从情理上能解释得通吗?
如果李时珍确实任过太医院判,那他儿子李建元在《进本草纲目疏》这份向皇帝进献的文书中,既提父亲“原任楚府奉祠”,又写父亲“奉敕进封文林郎、四川蓬溪知县”,却避而不提“太医院判”,那可是轻慢朝廷恩典,犯下欺君之罪,他有必要去冒这个政治风险吗?
李裕在考述李时珍在太医院任职情况时指出,明万历年间的两部医史著作,均未提到李时珍曾任太医院判。一是朱儒所撰的《太医院志》。朱氏是李时珍同时代人,掌管太医院事务多年,于万历十二年(1584)任太医院使时编成《太医院志》,后由太医院使罗必炜会同罗成名于万历四十四年(1616)校订刊刻,《院志》记录了在太医院任职或被举荐的人员,包括嘉靖至万历年间名医多人,但未见李时珍大名,这至少说明李时珍在太医院未获正式授职。二是明万历年间医家刘浴德所撰的《医林续传》。刘氏与李时珍同时代而稍晚,《医林续传》成书于万历癸丑(即万历四十一年,1613),这年刘浴德六十四岁,推算他生于嘉靖二十九年(1550)。《医林续传》所记明代医家达17位,其中《李濒湖传》可能是存世的第一篇李时珍传记,说李时珍为“医院吏目李言闻之子,永昌府通判建中之父”,不提李时珍任了什么官职。李裕认为,刘氏采用这种特殊的表达方式,显然是除了《本草纲目》已载明的之外,李氏别无高职。[13]
李裕认为李时珍在太医院未授官职[14],王宏彬则推断李时珍在太医院所任职务在八品御医之下[15]。笔者认为,李时珍被楚王府推荐到太医院,因到岗不久,所以未授官职,但他原任楚王府奉祠正,与御医(正八品)品级相当,所以人们仍以原来的官职称呼他;他供职不满一年即离开太医院,也就没有任命新职了。职场上将他以“原任楚王府奉祠正”对待。因此,清乾隆年间,大学士嵇璜等人奉敕编撰《续文献通考》,说“庆历间”(隆庆至万历年间),李时珍“官楚王府奉祠正”。[16]
郎需才认为李时珍未任太医院判,而是获赠太医院判。他说,李时珍的长子李建中被擢升为永昌府通判,府通判是正六品,院判也是正六品,后来,李时珍的孙子李树初按李建中的官衔为李时珍请赠;他又推测说,刻四贤碑时,石匠把“授”字位置刻得稍微偏了一点,本应刻在“山西副使”上面,却刻在“太医院判”与“山西副使”之间,这一字位置之偏,就成为后世学者们论争之源,顾景星的《李时珍传》和《蕲州志》说李时珍“授院判”就是受了四贤碑的影响,以讹传讹。[17]这里先辨析一下封赠问题。上文已谈到了明代封赠制度,按照制度规定,李时珍如果是因儿子李建中显贵而获得封赠,那应该是由儿子申请封赠,而不是由孙子申请封赠;李建中升云南永昌府通判,但实际未到任,因此不可能申请封赠,即使可以申请封赠,也只能是申请封赠“永昌府通判”,而不是“太医院判”;当时李时珍尚在世,只能是请封,而不是请赠;如果是孙子李树初请赠,只能是按照李树初的官职为祖父请赠。可见,郎氏所谓李树初按李建中的官衔为李时珍请赠,完全不符合明代政治制度。再考辨一下“授”字是否是石匠刻偏了。上文已论述了,光绪乙巳年所立的四贤坊表碑,其实是误以为“天启甲子”初立,所刻“太医院判李时珍”,源于顾景星的《李时珍传》和清代四部《蕲州志》的《人物志·李时珍传》,因此,“授”字并未刻偏,而是不合史实。
二、李时珍何时在太医院任职?因何辞职?
关于李时珍在太医院任职时间,也是众说纷纭。
王吉民《李时珍先生年谱》说是嘉靖三十年(1551),供职(任太医院判)仅一年。其论证逻辑是,据《白茅堂集·李时珍传》,李时珍辞去太医院判后,返回蕲州著《本草纲目》;又据《本草纲目·序例上》,李时珍自己说著《本草纲目》“始于嘉靖壬子”,即嘉靖三十一年(1552),所以将李时珍任太医院判系于此前一年。
吴佐忻《李时珍先生年表》说是嘉靖二十三年(1544)至二十八年(1549),供职多年。其论证逻辑是:据《白茅堂集·李时珍传》,李时珍到楚王府及太医院任职在前,撰写《本草纲目》在后,李时珍任楚王府奉祠正时,楚王世子暴厥(即抽风),被李时珍救活,推测李时珍于嘉靖二十二年(1543)治愈楚愍王世子朱英耀的病,次年,即嘉靖二十三年,经楚王朱显榕推荐去太医院任职;又据徐学聚《国朝典汇》卷七三《太医院》记载,嘉靖二十八年七月,礼部尚书徐阶参奏吴梦龙等人未经考试,凭借关系混进太医院充任医士,吴梦龙等人被革役为民,推测李时珍可能是由朱显榕凭私人关系推荐到太医院的,便托病辞职。
钱远铭主编的《李时珍史实考》说是嘉靖四十五年(1566)至万历元年(1673)。其论证逻辑是:光绪《蕲州志》说李时珍于嘉靖年由楚王荐于朝,那么《白茅堂集·李时珍传》所说的世子暴厥被李时珍救活,这个世子是指楚恭王朱英的世子华奎,还推测华奎生于嘉靖四十四年(1565)左右;光绪《蕲州志》又说李时珍于万历年任太医院判,《续文献通考》的《选举志》说“时以医举者……庆历间李时珍”,李时珍在太医院任职包括隆庆年间六年,直到万历元年;顾景星所撰的《李时珍传》两种版本,“数岁告归”与“一岁告归”均有道理,“数岁”是指李时珍在太医院任御医多年,“一岁”是指万历元年李时珍升为太医院判,任院判仅一年就“告归”。
笔者曾在《李时珍任楚府奉祠时间考》一文中指出,人们一般视顾景星《李时珍传》为信史,将其作为立论依据,因而,诸家所论李时珍任楚府奉祠时间经不起推敲。同样,上述各家论述李时珍在太医院任职时间,仍是陷入了顾氏《李时珍传》制造的谜团,因而也经不起史实检验。如,按照吴佐忻所论,李时珍二十五岁就治好了楚王世子暴厥,而顾氏《李时珍传》又说,李时珍十四岁中秀才,三次参加乡试名落孙山,那么,他放弃科举、从父学医时,当有二十三岁,他可能在短短两年之内就能独立行医,以精湛医术先后获得富顺王府、楚王府信任,并救活楚王世子吗?又如,《李时珍史实考》推测朱华奎生于嘉靖四十四年(1565)左右,而笔者在《李时珍任楚府奉祠时间考》一文中已考实,楚恭王朱英体弱多病,于隆庆五年(1571)八月初十薨逝,到隆庆六年(1572)二月左右,楚王府的宫人胡氏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(华奎、华璧),称是英的遗腹子。可见,《李时珍史实考》所推测的朱华奎生年,与史实相差甚远,那据此推论的李时珍在楚王府、太医院任职时间,当然也就不确切了。
笔者撰写《李时珍任楚府奉祠时间考》一文时,摆脱顾氏《李时珍传》的拘束,转换思维,另辟蹊径,以可靠史料为依据,论定李时珍于隆庆二年(1568)左右赴任楚王府奉祠正,又考定李时珍因为给楚王英调理身体,让楚王后继有人,大约隆庆六年(1572)夏,经楚王府推荐,李时珍得以进入太医院。
说李时珍于隆庆六年在北京太医院就职,是有旁证的。这年的中秋节,吴哲为李时珍写了一篇《题〈奇经八脉考〉》(相当于《序》),落款称“隆庆壬申中秋日道南吴哲拜题”。隆庆壬申,即隆庆六年。吴哲曾任兵部职方司郎中、河南布政使司右参议,隆庆五年(1571)九月,调任山西布政使司右参议兼按察司佥事,最迟于万历元年(1573)二月前,以山西右参议兼怀隆兵备道。隆庆六年中秋之前,李时珍与吴哲应当是交往了一段时间,否则,吴哲不可能于中秋佳节为李时珍的《奇经八脉考》作序。以职务上的限制,吴哲不可能离开山西(邻近北京)而远赴湖广,再加上交通条件的限制,吴、李两人也不可能在武昌或蕲州交集。这说明,隆庆六年有相当一段时间,李时珍是在北京太医院。《本草纲目》卷十五《草部·草之四》“麻黄”条记述:“一锦衣夏月饮酒达旦,病水泄,数日不止,水谷直出。……遂以小续命汤投之,一服而愈。”这则医案,或许可以表明李时珍最迟于隆庆六年夏即在太医院。
顾景星所说李时珍任太医院判与史实不合,但他将初稿中李时珍从太医院“数岁告归”,定稿时改为“一岁告归”,则合乎史实。李时珍在太医院供职不满一年,即辞职回乡。为何辞职,有的说是淡于功名利禄,辞职回蕲州专心著述;有的说是眼见吴梦龙等人被革役为民,便托病辞职;有的说是因为不受重用,于是借故告归;有的说是开罪了上司。依笔者浅见,这些似乎都不是,李时珍之所以辞职,是因为他的母亲去世了,他要回家处理丧事,还要为母守孝。按古代礼制,父母、祖父母死后,子女、孙辈必须守孝三年(实际为二十七个月),官员必须离职,称之为“丁忧”。
李时珍父母合葬墓的碑文,有“隆庆壬申十二月庚申日立石”字样。这月癸丑朔(即初一为癸丑日),庚申日为初八。查《中国史历日和中西历日对照表》[18],推算“隆庆壬申十二月庚申日”为公历1573年1月11日。这个时间,是李时珍和兄长李果珍为父母合葬墓立碑的时间。据李时珍《濒湖脉学》自序,其父李言闻于嘉靖四十三年(1564)之前即已去世;这个立碑时间表明,李时珍母亲张氏大约于隆庆六年十二月之前一段时间去世。可能是这年十一月,李时珍收到母亲去世的噩耗,于是便从太医院辞职,回家奔丧。到万历三年(1575)上半年,他丁忧期满,大约因为一是年近花甲,二是需要完成《本草纲目》的著述,于是不再请求复职。《本草纲目·序例上》说《本草纲目》“终于万历戊寅”,万历戊寅,即万历六年(1578),李时珍著成了集中国本草学之大成的《本草纲目》。因此,李时珍在太医院任职的时间,大致是隆庆六年夏季至当年十一月,不足一年。
李时珍长子李建中任职变动情况,也可作为李时珍从太医院辞职原因和时间的辅证。据乾隆五十一年(1786)本《光山县志》卷五《表三·职官》记载,李建中于隆庆年间任光山县教谕;又据康熙五十二年(1713)本《蓬溪县志》卷上《官守年表》,李建中于万历三年任蓬溪县知县。万历元年、二年,李建中未在外任职,当是在家为祖母守孝;服丧期满,李建中即由原来无品级的教谕,升任正七品的知县。他之所以能够升职,或许是因为,之前楚王府向朝廷推荐李时珍,为李时珍美言留下了一些余热,而李时珍又不要求复职,于是朝廷就将恩典赐给他的长子李建中。是否如此,当然有待考证,但有一点可以肯定,李时珍从太医院辞职,并不是因为在那儿不如意,而是因为慈母病逝了。
【注】
[1]《明史》卷七四《职官志三》。
[2]张慧剑:《李时珍》,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,第27页。
[3]吴佐忻:《李时珍生平年表》,中国药学会药史学会编:《李时珍研究论文集》,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版,第25页。
[4]唐明邦:《李时珍评传》,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,第348页。
[5]李裕所撰《李时珍生平考疑》(收入湖北中医学院科研处编:《纪念李时珍逝世三百九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文集》,1983年版),主笔的《李时珍和他的科学贡献》第十二章《关于李时珍的若干考证》第三节《李时珍任职考》(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版);郎需才所撰《评〈李时珍先生年谱〉》(载于《中华医史杂志》1985年第3期,又收入钱超尘、温长路主编:《李时珍研究集成》,中医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,第169、170页),《也谈李时珍任院判之争》(载于《湖北中医杂志》1986年第2期),《李时珍未任太医院判考》(载于《中华医史杂志》1996年第1期);王宏彬所撰《李时珍太医院任职考》(载于《亚太传统医药》2006年第9期),都对李时珍在太医院任职情况作了较为深入的考证。
[6]王吉民:《李时珍先生年谱》,载于《药学通报》1955年8月号第三卷第八期,又收入钱超尘、温长路主编:《李时珍研究集成》,中医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,第121页。
[7]钱远铭主编:《李时珍史实考》,广东科技出版社1988年版,第18—19页。
[8]参见拙著《荆王府史话》,华夏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,第154—161页。
[9]参见王宏彬《李时珍太医院任职考》。
[10]见顾景星《白茅堂集》卷三九。
[11]有韩国奎章阁藏本,邵懿辰(清道光、咸丰时官员,目录学家、藏书家)抄本。
[12]顾景星所撰《李树初墓志铭》说李树初曾“出知阳和府”,也与史实不符。明代并未设置阳和府。清顺治五年(1648)冬,投靠大清的原明朝将领姜瓖,在大同举兵反清复明,大同府迁治阳和卫(今山西阳高县),改名阳和府,顺治八年(1651),复名大同府,还旧治(在今山西大同市区)。所谓“出知阳和府”,当是“出知大同府”。乾隆四十七年(1782)本《大同府志》卷十《职官上》,就记载李树初于天启末期任大同府知府。
[13]参见李裕等合著《李时珍和他的科学贡献》第205页。按:李裕将罗必炜、罗成名并称院使,有误。万历四十四年(1616),罗必炜任太医院使,而罗成名时任上林苑监右监丞(正七品)管御医事,后官至南京太医院院判(据郑洪主编:《明清〈太医院志〉考释与研究》,科学出版社2022年版,第8、9、81页)。
[14]李裕等合著《李时珍和他的科学贡献》第205页。
[15]王宏彬《李时珍太医院任职考》。
[16]参见陈仕猛、段涛涛、王宏彬:《李时珍任楚府奉祠时间考》,收入《“明楚王墓与明代藩王文化”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,科学出版社2024年版,第22—33页。
[17]郎需才《也谈李时珍任院判之争》。
[18]方诗铭、方小芬编著:《中国史历日和中西历日对照表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。